林恩站在舞台的中央,聚光灯让他和战友们成为全场的焦点。
中场表演开始。
他的周围人山人海,闪光灯无数,
正前方“真命天女”组合正在高唱着。
林恩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还是会紧张。
华丽的舞台,全美国顶级歌手的表演,林恩的注意力完全没有被这些吸引到。
一束烟火腾空而上,璀璨的烟花将中场表演的气氛点燃。
就在火光炸裂的一瞬,林恩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战场上导弹爆炸的画面。
炸开的火光照亮了整个体育场。
林恩的目光跟随着烟火。
他神情骤变。
他的身体机械地踏着节奏,大脑一片空白,几分钟的表演时间对林恩而言如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此刻林恩的思绪仿佛回到了伊拉克战场上。
当舞台对面一颗烟花导弹直面飞过时,林恩的思绪便彻底在栽进伊拉克无法走出。
绚烂的烟花、多彩的灯光和欢乐的舞蹈,中场秀让一切看起来美好而荣耀。
这不仅没有让英雄林恩感到光荣,反而让他不断痛苦地回忆起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
没有人在乎这群军人的感受。
他想逃离这个虚伪的社会,回到真实的战场中去。
林恩,因为救战友的举动被偶然间拍到,同时所在的B班赢得了一场3分43秒的短暂胜利,一夜之间被奉为美国的英雄。
他们归国后参加各种宣传活动,最后一站是在超级碗,被邀请至球赛的中场休息时加入华丽的中场表演。
但对于林恩和战友们来说,这一天过得极为糟糕。
粗鲁无礼的球场工作人员叫嚷着驱逐他们滚出球场。
有的采访记者会问出无聊又可笑的问题。
追问林恩在战场上杀人的感受。
对杀戮机器感兴趣的橄榄球明星则不停地询问战场上部队使用的武器,杀伤力究竟有多强。
他们围观过来,睁大闪闪发亮的眼睛,一脸的好奇,正期待着林恩讲述杀人的感觉。
得知.50 机枪可以把人打成血雾,橄榄球队员们纷纷露出“帅呆了酷比了”的表情。
而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林恩忍受着黑人伴舞的嘲笑和侮辱。
在黑人伴舞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傻大兵”。
二货青年对于军人则是满脸的不屑,嘲讽军队中肯定有基佬。
中场表演结束后,林恩和战友们被遗忘在一边,没有人带领他们离开。
结果被场地的工作人员嫌弃碍事儿,撵他们赶紧滚蛋。
商人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恭维B班,为这场战役摇旗呐喊,却不愿意多付出一点点成本去犒劳这帮战士。
林恩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演绎的故事,在商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可以用廉价金钱收买的商品。
当林恩和战友们即将回到伊拉克战场上时,被看他们不爽的场地工作人员一顿暴揍。
台上,全美国为他们战争英雄的荣耀欢呼喝彩。
台下,对他们军人身份的戏谑和嘲讽,无处不在。
大家这群战场杀敌的军人们似乎只是一种标签化的崇拜,人云亦云罢了,并非发自内心对军人的理解和尊重。
19岁的林恩不是自愿入伍的。
他是给姐姐出头后为了撤销罪名而被迫参军。
他没有什么报效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英雄情结。
其实他就是个熊孩子,在军队违纪被队长惩罚,在简陋的操作室里坦白自己想要回家。
他现在在部队忍受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姐姐。
林恩救班长的动机很单纯,因为战场上生死之交的兄弟情。
与敌人近身搏斗也是本能的反应,在死亡面前没有多一秒思考的时间,所以没什么体会。
他也不想有这种拿生命做赌注的体会。
面对战争,林恩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19岁的孩子。
包括林恩的战友们,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人。
他们有的组建了家庭,有老婆孩子,也贪生怕死,并不梦想着做美国英雄。
有的战友因为战争患上明显的应激障碍,脾气暴躁,被舞台效果吓到后立即狂躁到要揍人,而且他动不动就想揍人用暴力解决问题。
他们每一个人巴不得早点脱离战争,享受正常的生活。
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
整个B班沦为爱国主义的工具,往返于形形色色的活动之间,回忆死去的战友,回忆战争残忍的细节。
这让林恩头痛到难以忍受。
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年轻人在战场上到底遭遇过什么吗?
“我所做的不是什么故事或者精神,是真实的生活”。
当心机商人想用低廉的金钱买断美国现役军人林恩他和战友们的故事时,林恩不卑不亢回怼了对方。
林恩所说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在伊拉克战争中,林恩和战友们要时刻迎接死亡的降临。
架上重型机枪,近在咫尺的敌人瞬间被打成鲜红的血雾,鲜血四射,骨头渣都没有剩下。
到处是残垣断壁,在这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每天必须要非常努力才能活下来。
一方面他们在战争里逐渐融入到伊拉克百姓的生活中。
像朋友一样聊天,开玩笑。
一方面要每天闯入百姓家里去搜寻可疑的恐怖分子。
只要搜到任何可疑的物品,手枪,萨达姆画像,涉及到军事的东西,那无论这个人怎么解释,都要戴上头套带走,然后很有可能被当成恐怖分子枪毙,再也回不了家。
伊拉克老百姓惊恐的神情,怒骂与哀嚎,改变不了什么。
这就是林恩在战场的真实生活。
除了战友,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林恩在球场上邂逅一位啦啦队美女,双方一见钟情。
这位小甜心倒是很能理解林恩,发自内心欣赏林恩,并且似乎也能尝试去感受林恩内心的痛苦。
林恩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
可是到最后,林恩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太过天真了。
当林恩即将回到战场,两个人难舍难分惜别彼此的时候。
林恩只是稍微透露出一点点不想回到伊拉克的念头,他一直在抗拒回去,也一直在纠结。
此刻啦啦队美女的反应却是: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怎么可以说不回伊拉克,你是英雄啊!”
啦啦队美女的神情好像是在诧异身为英雄林恩竟然有这种念头,前一秒还在卿卿我我,后一秒收敛笑容,只剩下满脸的质疑。
林恩只能苦笑着说自己在开玩笑,啦啦队美女才心满意足离去。
临走前还说道:
“我会为你祈祷的。”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林恩最终明白,那个主动投怀送抱,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人,也只是爱英雄这个光环。
啦啦队美女告别前说的话,和林恩嫂子说的话如出一辙。
也是将“我们一直为你祷告”挂在嘴边。
然而在她们心中,只有英雄林恩,没有林恩,她们祷告是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祷告。
这个中场表演,浓缩了整个美国社会。
林恩和战友们仿佛是消费品,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消费他们。
人们忘性大,在消费过后,谁还会记得他们?
只有墨西哥裔的服务员和经纪人阿尔伯特真正正视过林恩和战友们的个体身份。
前者以“自我”身份和林恩及战友抨击美国社会,去入伍不过是为了生计,捞点补贴,不用为保险发愁。
为国家卖命回来后,也只能在汉堡王打工,打回原形,重新回到起点。
每人说了一句“还能怎么样呢”,无奈又心酸。
后者理解和认同大兵的“自我”意识。
当林恩果断拒绝商人低廉的利诱时,有两句台词极为精彩:
“我觉得圣战徒都比您对我们有敬意。”
“有时候,没有倒比有一点更好。”
虽然林恩搞砸了经纪人拉过来的生意,但经纪人还是发自肺腑地尊敬林恩他们。
就连林恩的家人们,满脑子也只是想着林恩是为国争光,为家人争光。
林恩的父母,嫂子,都是伊拉克战争的拥护者。
林恩好不容易回趟家,他们关心的是战争的局势,是美国能否能占据优势赢得胜利。
他们认为美国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去救赎伊拉克人民,还给伊拉克民主,这让他们引以为豪。
唯独林恩的姐姐,众人皆醉而她独醒。
她是真的在担心弟弟林恩的生命安危。
她曾经从死亡边缘上走过,比身边的人都清楚死亡究竟有多真实多可怕。
对于她来说,死亡是车祸到来的一瞬间,对于弟弟林恩来说,就是一颗子弹飞过来的那一刹那。
她当然明白,与生命相比,加冕的荣誉根本就是一文不值。
在这个璀璨夺目的场地,人人口中欢呼的英雄不过是活在一个荒诞又虚伪的世界。
一场中场秀,几位所谓的“战斗英雄”的加入,其实是政治家的道具、商人的商机、各行各业的人随意参与的自嗨。
而真正属于林恩和战友们的真实世界,是在伊拉克。
那里枪林弹雨,才是军人的天职所在。
讽刺的是,战场才是林恩和战友们认为的安全的地方。
回归战场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没有人热爱战场,没有人愿意面对死亡。
最后,林恩拒绝姐姐想让他退出部队的提议,选择回到伊拉克。
不是出于英雄主义,或者爱国。
他只是感觉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找到了自我。
他不属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下没有办法找到自我,所以回到部队才是最好的选择。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林恩和战友们的发现,现实是比战争还要恐怖的地狱,他们要逃离,回到最真实的地方。
这是一部非传统意义上的反战片,直戳着美国社会的痛点。
壮观的超级碗,豪华的秀场,灿烂的烟火,超级巨星……
上层社会的人们代表盛世美国,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挥金如土享受着顶级娱乐赛事。
而林恩和战友们死的死,伤的伤,即使身体健全地活下来也要大概率面对陪伴一生的精神创伤疾病。
他们看似被全美国视作英雄,人人称赞他们,敬重他们。
实际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以此鼓励更多的人也变成为资本牺牲自我的工具。
真实的美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发动伊拉克战争,打着民主的旗号,去夺取石油资源。
林恩姐姐这个角色直接说出美国上层社会的虚伪,令人厌烦:
“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他们这么想打仗,应该自己上。”
不少人感觉这部电影带有强烈的反美色彩,狠狠打了美国的脸,冒犯了美国人根深蒂固引以为豪的精神所在。
所以四年前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时,口碑不怎么样。
美国主流媒体差评不断,烂番茄指数只有43%。
电影在美国上映后票房惨败,只有区区170多万美元的收入。
这也成为李安第一部口碑票房双失守的作品。
但放到今天再看,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程度。
国家现在一片混乱,而美国政府却还有心思想着怎么甩锅,每天上演着各种荒谬的戏码。
不知道疫情之中的美国人还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骄傲可言?
不得不说,四年前的李安太勇敢了。
拿着美国资本家的钱骂了资本家,说出了美国人最不想听的话。
而且在我看来,李安想要表达的并不只有这些。
在娱乐时代下,个体权利与群体利益之前的冲突矛盾,资本通过消耗、剥削、扩张等方式来实现市场的循环。
资本的上层永远是一片虚假的繁荣,底层的个体则永远被社会所忽略。
这样的国家,不止美国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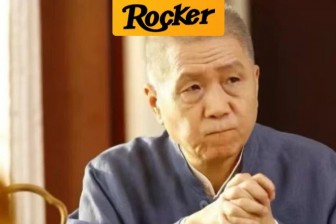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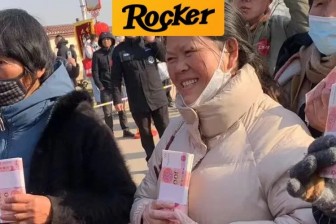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