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自诩是中国电视史上讲会黄段子的鼻祖,靠着一张嘴,主持着国内最好的脱口秀节目,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他的节目被誉为国内电视节目的良心,看似装疯卖傻,嘻嘻哈哈,实则铿锵有力,敢说敢言。
他就是主持人窦文涛。
滚君重新回过头去看窦文涛的节目,发现他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一个符合主题的黄段子,引得嘉宾哈哈大笑,但又不显得低俗。
99年王菲第一次上《锵锵三人行》,他们聊到男女择偶问题时,窦文涛突然脑子一转特别自然地讲了个百货小姐的段子,把王菲逗得前仰后合。
窦文涛讲完一个,王菲起哄还要他再讲一个,她说她就爱听窦文涛讲笑话。
后来又在节目中说到东莞发展时,他说自己很符合这所城市的形象,可以去当代言人。
他还调侃说《锵锵三人行》的命运和东莞很像,都是一开始靠黄色吸引眼球。
窦文涛是个聪明人,却不卖弄聪明。无论是说黄段子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是他做节目的方法论。核心点只有一个——要说人话。
其实从节目里就能看出来他懂得很多,爱玩古董字画,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
但他身上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傲。
他对于现在的新兴文化更多地是包容和理解;他不爱说教,更多地选择用幽默和段子去解构每个现象。
因为他也深知,现在这个时代说些大道理没用,讲两个段子呵呵一笑可能反倒有人会思考其中意味。
1996年,窦文涛来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时候他正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电台节目《今日热线》,偶尔还去广东电视台兼职主持人。
他本来想说申请调去电视台工作,电视台台长都答应要他了,结果电台的领导却不放他走。
一盆凉水把窦文涛浇了个彻底,他就被不尴不尬地晾在那儿了。
左边窦文涛,右边赵彦红
当时香港正在秘密筹办凤凰卫视,没有公开招人,也没有在社会上发放什么消息,只是几个核心的人员来办。
有一天窦文涛在电台大院饭堂里打了一盒饭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接到电话,说要在香港成立一个电视台,一些内地人和香港的卫视中文台合作。
当时他就有一种直觉让他必须答应,他捧着那个饭盒,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说:“我去。”
一起去凤凰卫视的还有许戈辉和陈鲁豫,后来都成为了当家主播。
三个年轻人远赴香港追求自己的电视梦,互相依靠、互相支撑。
直到现在他们也依然是为人津津乐道的“铁三角”。
窦文涛总是满嘴跑火车,将她们俩称为自己的两代“玉女”,他们是相亲相爱的小三口。
当时的凤凰卫视都是女主播,他是为数不多的男主持人,所以他一直就是和女孩子玩,插科打诨,调戏聊骚。
和许戈辉、陈鲁豫曾在一张床上睡过的故事讲了十几年。
他现在也说:“我爱戈辉!鲁豫也行。”虽然许戈辉已经是孩子的妈了。
1996年3月21日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的日子,当时卫视有一个王牌节目《相聚凤凰台》,他们三个都是从那个节目中走出来。
还是新人的窦文涛手上只有这么一档节目,日子过的很轻松。
一周录制2天休息5天,没事吃完饭就和许戈辉、陈鲁豫三个人逛大街。
后来,窦文涛无数次表示那段日子是人生中最轻松愉悦的时光。
“没那么多想法,内心没有太多欲望,感受不到太多责任。”
窦文涛去香港看似义无反顾,其实时刻在担心自己饭碗不保。
其他的主持人签的都是艺员合约,他主动要求签了艺员和撰稿人两份合约,就怕突然把他辞退了自己还能有条退路,做个幕后。
他就这么做两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干了一年。
凤凰卫视发工资是装在信封里,那一年每次窦文涛拿着工资信封都半天不敢打开,生怕一打开是封辞退信。
看到是工资,他就有种又熬过来的感觉。
窦文涛说:“我这脸,从没想过能在电视台做主持人,我播新闻别人都觉得是假新闻。”
有句老话叫“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窦文涛做电台主播拿到了最高荣誉“金话筒奖”,做电视也依然很有天赋,他在凤凰卫视达到了他的事业巅峰。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正式回归日,而从6月30日起,两国仪式性的直播就已正式拉开序幕。
于是凤凰卫视推出了一档“60小时说不停”的栏目,不间断直播香港回归的整个过程,这极其考验主持人的语言功底和反应能力。
一共有6个主持人,窦文涛是从头撑到尾,一人就说了6到8个小时。
也是这一场直播让台里领导认识到这个在《时事直通车》里一本正经说新闻的小伙子说话的本事特别大。
1998年,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打算办一档低成本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人选看中了窦文涛。
节目取名为《锵锵三人行》,取自“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其实节目的最初定位是严肃的时事评论,这类节目当时太多了,讨论一个社会问题,请相关专家谈论一下看法,是惯用套路。
但当时台里的条件不允许,找不到这么多嘉宾,只能是固定三个人聊。
窦文涛就主动给领导写信,想把节目做得像朋友聊天一样,非线性无主题,想到哪说到哪,还给这种想法起名叫“海天主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虽然他后来每次提到“海天主义”都觉得傻得要命。
98年3月,窦文涛走进凤凰卫视的录影棚里第一次录《锵锵三人行》。
4月1日,第一期节目开播。
窦文涛褪下播新闻时的严肃,在节目里谈笑风生,他反应很快,随口就是一个段子。
其实后来窦文涛说,他确实当时有在认真研究黄段子,并抄录在案,但是自己并不是有意识地去说。朋友闲聊间会提到这些,他“无知者无畏”,想到就说了。
他和《锵锵三人行》打破了当时主持人和时事评论节目的严肃形象。
当时的观众说:“终于有个不装的节目了。”
窦文涛第一次让中国电视开始“说人话”。
《锵锵三人行》一开始情况并不理想,开播半年都没接到广告,本来按凤凰卫视的规矩是要被砍掉的,但当时刘长乐在会上说文涛不容易,这个节目给他留着,就这样又留了一个月。
后来,窦文涛靠着他那张嘴一炮而红,节目也在文化圈里占据一席之地,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众印象里的他是这样的:一脸坏相,笑起来色眯眯的,在节目里油嘴滑舌,谁说的都对,爱装傻,也爱说黄段子,没个正行。
因为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他不想塑造一个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形象。
“我的专业不是观点,我的专业是介绍观点,我才无所谓你这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我关心的是你这个观点聊得有没有意思,除了极少数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对大多数事情是没有观点的。”
窦文涛是个了不起的主持人,刘长乐说他在节目里是在“仰视观众”。
他无疑是个聪明人,对事物看的也很透彻,但在节目中很少表现这一点。偶尔在节目里的一次发言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但比起说,他更愿意倾听、引导。
这么多年的节目经验,他早就学会剥离自我情绪和价值观,每一个问题都站在观众的角度上思考,所以观众才有参与感和代入感。
18年6月,一段窦文涛采访俞飞鸿的老视频截图上了热搜。有人发微博称俞飞鸿是老男人照妖镜,大骂窦文涛、冯唐、许知远直男癌。
原因是因为窦文涛问俞飞鸿为什么总是单身?一个人会不会寂寞这类问题。
其实窦文涛跟俞飞鸿很熟,两人是“闺蜜”关系。他怎么会不了解俞飞鸿的想法?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厌恶婚姻制度。
这些问题都是他替观众问的,也是给了俞飞鸿一个向大众表达自我的口子。
被骂的锅他就自己背了。
《锵锵三人行》是直播的录制方式,好或者不好都是一次过了。节目之前他们会有所准备,但录制时大部分还是靠临场发挥。
十八年的节目,来来回回上百个嘉宾,有人说的多了、跑的远了,有人不知道该聊些什么,有人话说过了差点越界,有人不肯敞开聊。
窦文涛就凭自己一张嘴,把节目内容聊的有滋有味,戴着“镣铐”在圈子里跳舞。
“我觉得是一种极其专注的分散,脑子里同时有八匹马在跑,就像你在操纵着一部复杂的机器,这儿一个按钮,那儿一个指标,你什么都要看。”
他要倾听每个嘉宾的发言,说得快越界了就赶紧拉回来,要冷场了就自己多说两句,氛围太严肃了就说两个段子。
窦文涛将自己在《锵锵三人行》的主持比作画画,有主题但是没有目的。他把这当做一种游戏,在其中享受到乐趣。
他越来越火之后,还延伸出了很多其他节目,《文涛拍案》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锵锵三人行》,但这档节目也没有坚持很久。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文涛拍案》是录播,可以无限次重来。他就一遍不满意再来一遍,一次次重来把工作人员都熬睡着了。
这对他而言慢慢变成了一种折磨,最后还是选择辞掉这档节目。
窦文涛人生中坚持最长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那张小桌子前录制《锵锵三人行》。
但2017年9月,《锵锵三人行》官方微博发声明称将无限期停播。
但还好在17年1月份的时候窦文涛的《圆桌派》就已上线。
由原来的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
嘉宾变了,但形式和窦文涛依旧没变。
他在节目里还是抛梗不断、插科打诨,兴起时甚至手舞足蹈。
显然他的这种风格非常适应现在网络综艺和年轻人的步调,节目受到很多年轻用户的追捧。
与他风格极端不同的是《十三邀》的许知远,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
总是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娱乐和技术现状带有怀疑和偏见,总是忧思艺术审美的未来。
有人说窦文涛装疯卖傻,说他看起来就不像好人,但很少有人说他“讨人厌”。
在那帮传统知识分子质疑、不安的时候,窦文涛已经和这个时代融合的很好了。
其实这也与他本身的性格分不开。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为社会呼吁的,我也很早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窦文涛说,“我跟Google差不多,我尽量别作恶,对吧,但是呢,我还是要活我自己,大多数人跟我没什么关系。”
他其实私底下有点自闭,有与人交际的能力,但没有与人交际的兴趣。
更多的时候,他就自己待在家,喝茶看书画画写字,他总说在家里有很多事情做。如果可以的话,他只想泡在故纸堆里。
他也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些过于凉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种话他是从来不会说的,因为他觉得观众就是观众,不是朋友。
窦文涛是个文人,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
他爱老东西,他也对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感到忧虑,但他只默默放在心里,折磨自己,很少站出来大声呐喊。
“很多人总想着靠自己去改变世界,我特别不理解这种人,你好好活着,干嘛非要去改变现在的世界呢?你好好在家待着跟家人吃吃饭,喝喝茶,做点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改变世界?世界没了你照样也运转得好好的,有很多人总是打着这种大气去干一些蝇营狗苟之事。”
窦文涛有一种“小家”的思想,他深知无力改变世界,所以他和这个时代和谐相处。
这种思想也被带入他的节目中,从《锵锵三人行》到《圆桌派》都只讨论,不说教。
他明白说教也没有用的,一晚上过去观众就忘了他们说了什么,还不如让观众多笑笑,至少当下的开心是真实的,能有所思考当然是更好了。
媒体人胡赳赳曾这么评价窦文涛:
“窦文涛说人话、鬼话,但不说神话。窦文涛说讨好的话,但不说卖乖的话。窦文涛说聪明而卖弄的话,但不说愚蠢而不自知的话。窦文涛说反讽的话,但不说愤怒的话。在娱乐受众的同时,他自己身心也得到清洗,受众在被娱乐的同时,发现愤怒已被消解殆尽。”
这是我听过对他最好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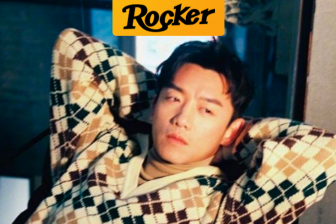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