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丁地处偏远,自从色情产业没落后,这个小镇的经济就一蹶不振。
大批失业者游荡在街上,小酒馆里坐满醉生梦死的老酒鬼,每天都有苦闷不堪的人亲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科特·柯本就出生在这个落寞的小镇。

他的父亲是机械工,母亲是服务员,一家人原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这一切都因为父母离婚而支离破碎。
柯本8岁时,爸爸妈妈开始陷入无尽的争吵中,甚至大打出手。他们把柯本当做威胁对方的砝码,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
柯本的性格开始变得沉默、孤僻、阴郁,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小小年纪的他在墙壁上狠狠写下:“我恨妈妈,我恨爸爸,爸爸恨妈妈,妈妈恨爸爸,这真TM让人难受!”
14岁生日那天,舅舅送了他一把二手电吉他,虽然拾音器有点毛病,但他依然如获至宝。
从此他开始疯狂练习吉他,一个星期就学会了AC/DC的《Black in Black》,迫不及待尝试自己写歌,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摇滚巨星。

摇滚乐拯救了颓废的柯本,成为他精神上唯一的支柱。长期的抑郁只有在摇滚乐中才得以释放。
可惜,小镇里没有人听摇滚乐,柯本沉浸在一个人的摇滚狂欢里,从未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后来,父亲无法忍受他的冷漠乖张,把他寄养在基督教家庭,不闻不问。
每周三晚上,柯特都去基督教青年团参加活动。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Krist Novoselic。

Krist两米多的大高个,总是沉默寡言,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经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沉浸在练琴中,几乎不与外界交流。
他有个怪癖,即使背带不够长,也要坚持把琴挂得很低,甚至给背带加一段绳子。可以说是十足的闷骚了。

除了同样热爱摇滚乐,Krist也是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有着和柯本极其相似的经历。
命运的安排难以捉摸,但孤独的灵魂总会在摇滚乐中相遇。
曾经的柯本在绝望中挣扎,在即将溺水的一刻,他遇到了Krist,一个同样受伤、同样被摇滚乐治愈的朋友。
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死党,聊音乐,聊生活,亲如兄弟。
1985年,他们找来鼓手,三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掀起全球Grunge浪潮的传奇乐队——涅槃。

这支乐队诞生后,迅速收获全世界青少年的狂热追捧。
柯本粗粝颓废的嗓音,刺耳的吉他,狂躁的鼓点,涅槃乐队用极端消极的态度否定自己,也抵抗着这个无能为力的世界。

这种无路可退的绝望呐喊,恰好映照出当时年轻人普遍的心境。
这群生长于美国价值观混乱的一代人,不再从毒品中寻找安慰,而是在涅槃的音乐里释放愤怒,找回迷失的自我。

涅槃乐队所有的传奇故事,都始于柯本和Krist的相遇。两个孤独而热血的灵魂,在摇滚乐里找到自我,也在摇滚乐里和彼此相遇。
每一个摇滚客都是孤独而有趣的,只有摇滚乐响起时,他们才能嗅到同类的味道,彼此相认。

类似这样因为摇滚乐相遇的故事数不胜数。
滚君曾经采访过黑撒乐队,主唱曹石讲述了他和王大治相遇的经历。
当时研究生毕业的曹石在某公司实习,没日没夜的加班让他殚精竭虑,甚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无比厌恶这样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乐队另一个主唱,王大治。两人心里都怀着摇滚梦,直到认识彼此,才勇敢做出决定——我们要开一间音乐工作室,为西安的独立音乐人录音、做唱片。
他们也组成了自己的乐队,创造性地用西安话唱摇滚,独特的韵律、亲切的口音,竟然收获不错的反响。

那段时间,曹石过着AB面的生活。白天是大学老师,晚上回到工作室玩乐队,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自如。
有时候学生们会故意逗他,“老师,你能给唱个歌吗?”曹石绷住笑容,假装十分高冷地拒绝,“不行!”
滚君还有一位朋友,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典型的“斜杠青年”。
他白天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敲代码。一到晚上,他就背着吉他“潜入”酒吧,在舞台上像变了个人似的,大步一跨,疯狂扫弦,在暴烈的节奏中释放自己。

但他也有小小的遗憾,就是至今仍然是单身狗。
他说,他最羡慕的一支乐队就是简迷离,两个人因为摇滚乐相遇、相恋,跨越国籍的障碍,成为人人羡慕的夫妻档。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学甚至从高中开始就尝试自己组建乐队。
和所有年轻的乐队一样,他们没有唱片公司、没有赞助商,只有简陋的设备、简陋的排练室、简陋的舞台……唯一不简陋的或许就是自己写的歌。
滚君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
“在大学组乐队,组的其实并不是乐队,而是一种羁绊,是一群人像战友一样,共同去对抗这个世界的羁绊。”
不止摇滚,其实每一个孤独的人都希望遇到理解自己的同类,拥有羁绊。
最近看到的一个歌舞片,就把这种遇到同类的雀跃感用鲜艳的色彩和欢脱的舞蹈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还是深夜陪伴观众的主播,又或是执着于摇滚梦想的乐手……
他们似乎轻轻松松,推开门就能遇到同类,看完你只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正是因为我们热爱的东西都是如此的独特而又孤独,才会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彼此,找到同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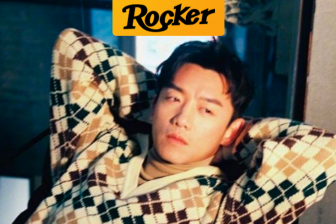



评论